2015年六月份我高二的时候,突然发现自己脸有点肿,当时以为是紫外线过敏,过了半个月脚也开始肿,我妈带我在我们当地的县医院检查,理所当然,查了三天什么都没查出来。
第二天,我们就去了沈阳最好的医院住院检查,查了一段时间,确诊“库欣综合征”,但是始终找不到是身体哪块出了问题引起的,做了特别特别多的检查,发现有三个地方可疑:1、脑垂体;2、肾上腺;3、胸腺。脑垂体和肾上腺是常见的引起“库欣综合征”的源头,当时也说青少年在胸腺上长小瘤问题不大,时间长就会自己吸收(大概是这样,记不清了),但是当时我整个人症状已经很明显了(具体可以百度),而且马上进入高三。爸爸妈妈决定先做胸腺的手术,如果不是这的问题那就再查。然后等咨询医生的时候,医生给的方案是,只能大开(也就是从脖子开刀,最后会留下一条二十几公分的疤),我们都犹豫了,医生建议我们去北京协和看一看,但是当时好像还没有高铁(记不清了),而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坐那么久的火车了。这个时候,对中医颇有研究的大姨夫说,你们先回来,我给开点中药先控制一下。这个时候我在沈阳已经住院28天。
然后,我们带着一堆病例和片子回家了,想想我当时还挺爱学习的哈哈哈,回家以后我还把暑假作业写了。嗯...这个病会让人情绪非常不稳定,而爸爸妈妈都要上班,然后奶奶和姥姥就换着来陪我,怕我想不开。那个时候确实很有可能想不开,一天三餐吃素,严格控制饮食,喝中药,甚至小便都要接在桶里测量数值,而且严重便秘。
从回来开始,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就开始在网上挂北京协和的号,但是真的太难了太难了,后来妈妈找到了加号,把病例发过去以后,北京协和同意了我们的加号申请,第二天我们匆匆赶往北京,到了才知道我住的内分泌病房,一年内分泌患者十万多,但是床位只有六十多。我们成功看上了病,然后医生就让我们等床位,说来我也是真的幸运,那个时候正好中秋和十一连起来了,所以内分泌病房正好空出来床位,上午医生让我们等床位,下午我就住进去了。来到北京一周我就住上院了。
然后就是各种检查,我的病情也是一天一天肉眼可见的加重了,虽然当时也是实在不敢确定手术的位置,但是也还好有果断的妈妈,她说,就做胸腺的手术吧,有什么后果的话我们自己承担。因为当时协和的医生可以做微创,而且实在是太严重了,手术前几天的时候我开始流鼻血,喘不上来气,手术前一天只能躺在床上吸氧。
我是当天的第一台手术,手术时间比预计长了很多(因为我的血压一直下不去,麻醉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,换一家医院的话可能会暂停我的手术,让我把血压降下去再手术,因为血压高真的是很危险,那我现在可能就嗝屁了哈哈哈),手术后直接进了ICU,各种并发症同时找上来了,重度呼吸衰竭,重症肌无力,肺孢子虫...我的肺一度在x光片下只能看见白花花的一片,我在ICU一待就是四十几天,呼吸机理论上是只能插十几天的,如果再不能自主呼吸就得切开气管,但是由于我用了ECMO(也叫人工肺),不能止血,医生们就没有切开我的气管(所以刚拔了呼吸机那天,我整个人是合不拢嘴的,口水流了一天,第二天才能讲话)。我三次被下达病危通知,最后一次我真的差点挺不过来,妈妈找来了红十字协会说要捐器官,被我的主治医生拦下了,他说:这是一个16岁的孩子,正是最好的时候,既然你想捐器官,那我很相信你们的人品,我试着用新型的方法治一下吧(大概这个意思)。
奇迹真的就发生了,我一天天好转,经过北京协和三个半月的治疗,我活过来了,我甚至还打破了协和的人工肺时长记录(哈哈哈叉会儿腰)
住院期间也碰到了很多病友,她们的故事以后再慢慢写。总之我想说,北京协和真的很牛,我遇到的每个医生真的是我们心目中医生的样子,治病救人,一心一意为患者着想。
而且北京协和的护士姐姐们也都真的很辛苦很细心很温柔!!!
写完这篇的第二天!
我一定要说!我找到我的医生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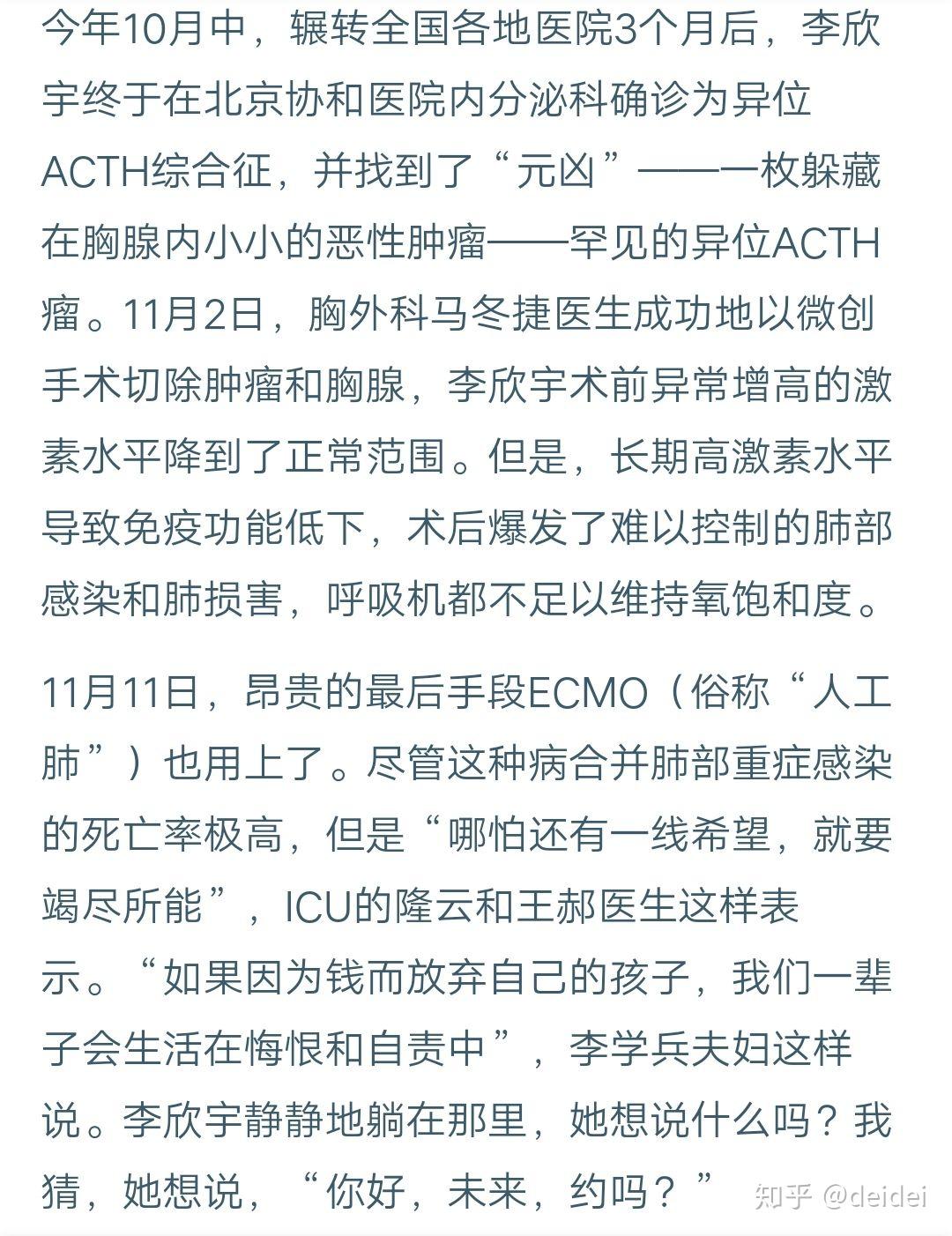
(这是秦应之医生帮我发起的腾讯公益的截图)
我真的要哭了!
今天早上,王郝医生回我了!他还记得我!快乐地转圈圈~
看有好多人都在说费用的问题,费用确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,但是也没有特别特别低,是因为当初医生们帮我在腾讯公益发起了捐款,住院时候认识的病友,我的高中同学,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心人都在雪中送炭,所以没有在资金方面太过为难,谢谢大家关心呀 ~
想起了治病中的一个检查,“岩下窦采血”,是一个小小的介入手术。是半麻,从大腿根部伸一根针进去,进到脑袋里面去取血。我记得在沈阳做的那次,我只做了一边的腿,因为生病,我的血管特别脆、细、深。当时我躺着手术床上我是能感觉到嘶嘶的取血的声音的,也疼,但是当时我一动也不敢动,过了很久,我听见取血的医生说:这哪是岩下窦啊,这是岩上窦!(我以为他们不是在说我),然后我就听见他们出去了,再后来就是给我夹上了止血钳,夹了整整二十四小时。
等我被推出去都时候看见妈妈在哭,后来我才知道我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,中间医生出来说粗管进不去要换细的管,让去缴费(八千)妈妈想到我受的罪就哭了,这个时候医生又说管进去了,再然后就是我出来了。
止血钳取下来我的腿淤青了一大片,很长一段时间走路都很难受。
然后在协和检查的时候,我们拿出来了在沈阳做岩下窦的结果,医生说:这结果根本就不对!我才后知后觉,原来当时他们说的真的是我。
在协和做岩下窦采血的时候,妈妈说,直接用细管吧,医生说:相信我们,粗管就可以(这次做两边,细管和细管差八千块钱)。然后就真的可以了,两侧都做完我还想说咋这么快,就听见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说:哈哈哈我给你省八千块钱。但是当时我不敢说话,毕竟脑袋里还有针hhh。做完以后医生就在我的腿上针眼的地方各包了一个纱布,说六个小时之后下床就可以。
一个检查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
那你说:协和是不是很牛! |